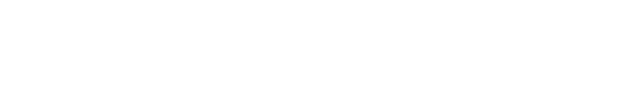联系我们
二○○一年五月八日,八宝山陵园大礼堂内,一片肃穆,人民抬著、灵柩缓缓行进,中间挂著一条白色的黑底白幡,上面写著「对的深切哀悼」,下面是一张慈祥的长者的画像。
的长子李和平,二儿子李南征,二个 女儿李远征,李优优,全都在旁边哭成一片。
来宾陆续到场,将军儿女含泪与来人握手感谢,毛主席之女李讷、女婿王景清等也都不顾自己身体不适,亲自到场,为献上花圈,为他默哀。
从新县赶了过来,乡亲们眼泪汪汪的说:“老乡们来给您送行了!将军,安息吧!”
在摄像机前,新县的乡亲们也表达出了自己的心愿:“愿将军回乡,新县有五万多烈士,等着您回来呢!”
在军旅生涯数十载,无论身居什么职位,都是一副淡然自若的样子;但是,长期远离故乡的游子,在“无官一身轻”的思念中,始终萦绕着对生他养他的故乡的思念。
的老家位于大别山腹地,位于河南光山县柴山堡(属新县)的李家洼小山村。
李家洼很穷,也很偏僻,周围都是大山,唯一的出口就是一条狭窄的小道。自出世起,便尝尽了贫苦人家的苦楚。在妈妈的安排下,七岁就拜一位裁缝师傅为师。
那时候,做裁缝的都是手工活,比起种地,要轻松许多,她妈妈的愿望就是让他多学几手手艺,将来能扛起这个家。
然而,年轻的并不了解妈妈的辛苦,他总是感到自己整天被关在屋子里,替师父做些杂务,什麽都没学会。所以,他告诉妈妈不要做裁缝,而要放牛。
那个时候,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放牛是没有工资的,只是勉强糊口而已。无论风吹雨打,烈日炎炎,牧童总是要把他的牛群赶到山林里、草场里、小溪边,吃些苦,也是难免的。
牛主人的老婆婆脾气很坏,常把残羹冷炙送给,若她嫌牛儿不够,便不准吃饭。相较于学习缝纫,放牛是很辛苦的,然而生性活泼的,还是比较享受这样自由自在、自由自在的日子。
贫穷家庭的小孩,很早就离开了快乐的童年,在的记忆中,最让他无法忘记的,就是他总感觉自己永远都不能填饱肚子。
由于家境贫寒,他从不过自己的生日,甚至连自己的具体生日都不清楚,直到通过远方的伯父伯母,他才得知自己是1916年五月生的,至于他的生辰八字,却无人能说得清楚。
在1928年6月,苏维埃政府成功占领了柴山堡地区。紧接着的一年,李家洼地区诞生了一个儿童剧团,在众多团员中脱颖而出,被选为“少年团”的领军人物。
当时虽然对革命理论了解不多,但是他那朴实的阶级情感,却是他走向革命道路的向导。
当时他们的主要工作,就是望风、查路、打砸庙、。与那些“小打小闹”相比,更乐于承担为红军传递情报和传递情报的重任。
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,因为他从来不走大道,而是走山间小路,既隐秘,又快捷。童子团是遵照苏维埃政府规定的,戴着臂章,戴着一条小小的领结,参加各种活动。
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木棒,一端涂着黑,一端涂着红,孩子团的人管它叫“红黑不认人”,它的意思是,凡是触犯苏维埃条例的人,都可以用它来管教。
背着一根棍子固然威风,却有一个远大的抱负,那就是要成为一名红军,到真实的战场上去战斗。
在少年团为红军写书信和领路的过程中,结识了许多红军官兵。他注意到,红军中有许多士兵,他就想成为一名士兵,于是就向他的舅舅李家辉提出了这个要求。
李家辉那时在乡团委任书记,乡苏维埃主席也姓胡,李家辉在学习篾匠的时候就拜他为师,所以他有权让村里的年轻人加入红军。
很快,一位红军营长找到了,李家辉急忙叫,要求他亲自加入红军。
那个营长听说当了童子军的队长,对他十分喜爱,可是看他年轻,便踌躇不决。
营长把看得又看又看,心中一动,指着旁边的通信员便向示意,“你去和他比赛,打得过他,我就把你带走。”
听到这一条消息,立即把传令兵往前赶。打小就放过牛,爬山跑路什么的,那都是轻而易举的事,反倒是通讯兵,扛着一包弹药,就不太方便了。
不过,这还不算完。随后指挥官询问在逃跑过程中听到了什么,看到了什么,犹豫了一下,然后把自己所听到的和看到的都告诉了他们。
营长很高兴的回答,并允许他加入军队。于是,十四岁得便独自一人完成了他的红军梦想。
解放战争中,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六纵十七旅的团长,而他的上级就是大名鼎鼎的“疯子将军”王近山,也就是后来被称为“狂人”的那个人。在那六纵之中,麾下的第十七旅也是最为精锐的一只。
在长征途中,追随刘邓主力冲破黄河的天堑,千里挺进大别山,与中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,当率领部队包围大王庄时,正专心研究地图的忽然把地图放下,跑到外边查看战况。
结果他刚刚离开指挥部,就看到一枚巨大的炸弹从天而降,直接砸在了旅指挥部所在的屋子里,作战科长、作战参谋、通讯人员等都死了,只有他一个人安然无恙。
上甘岭之战打响以后,坚守坑道的第十五军因敌人猛烈的进攻,损失严重,后勤补给严重不足。
王近山心事重重,他以第三军团的权威身份,倡议设立“五圣山指挥部”,推举担任总指挥,负责领导三十一师团与四十五师团的反击行动,同时,二十九师团提供支援,整个作战由第十五军团总司令亲自统帅。
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,的前任政委杜义德曾经说过,这次的部署,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换汤不换药,以十二兵团的兵力去对付十五军的仗。不过并没有抱怨什么,他来到兵团后高兴地接受了命令。
王近山三天三夜没合眼,把打发走之后,直接往被窝里一倒,对杜义德说道:“让上来吧,我也能安心地睡一觉了。”
到达司令部后,的命令迅速而果断,对于人员的分配,他是一视同仁的。那是由于在上甘岭上驻扎着十五军团和十二军团的士兵。
在用人方面,我们不搞“山头”,而是“任人唯贤”。其次,要从大局出发,进行具体的操作。他对整个局势了如指掌,对一条隧道、一座阵地、一支小部队都了如指掌。
就是这么把十二、十五两个兵团的人团结在一起的,他们的力量是一致的,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。在这一战中,我们不负众望地击溃了“联合国军”,歼灭了两万五千人,取得了一个辉煌的胜利。
新中国建立之后,进入南京军校,在军校,对现代战略和战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。学成归来,又回到了自己的部队,并一直在军中任职。
回到部队后,便着手学习练兵之道,协助祖国建设一支正规、现代化的军队。一日,到山下去视察,看战士们操练。
看着看着,他就发现有一个连的表现很出色,远超于了别的连。有些奇怪地问了一句:“你今天的表现挺好的,平时都做了些什么?”
士兵们被他这么一捧,脸上都有点挂不住了,纷纷看向:“这哪能怪咱们,这都是咱们副连长教导有方啊。”
接着问道:“哪位是你们的副连长?”士兵回答:“我们的副队长叫郭兴福,平日里带我们的就是他。”
所以,便让人将郭兴福找了过去,和他谈了谈,希望他能给自己讲解一下自己的训练方式。
听了郭兴福的话,然后看向了郭兴福:“你这种授课方式非常好,我们国内目前正缺乏这种科学而又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,你是不是能够将这种方式带到军队中,为祖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?”
郭兴福一听,顿时一脸兴奋:“我当然要去,为祖国培养更多的军人,这是我的梦想。”
在的指导下,郭兴福教授的教学法在各连班试用,效果明显。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归纳,并将其称为郭兴福教学法。
郭兴福教育学生的方式对提高军队的综合素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毛主席得知此事后,称赞说:“这种教法很好,应该在全军范围内推广,并且要嘉奖那个想出这种教法的人。”正是从这一点上,被毛主席看中,被毛主席看中。
在九十年代,为了国家的事业,奔波了大半生的,总算可以退居幕后,安享晚年了。
他又一次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家乡,他的父母去世的很早,所以他对家乡的感情很深。
再一次回到故乡,300年树龄的银杏依旧郁郁葱葱,尽管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但贫穷的状况仍然没有正真获得改善。
他跟村民们聊得很开心,但一听说这些年轻人,都去种地了,或者去打工了,他就有些担心了。
一生中最后悔的事,就是在私塾里念了数年书,他明白,要想改变这样的情况,唯一的办法,就是学习。
把自己多年的薪水都拿出来,并带头发起募捐,帮助村里办一所小学。受他的影响,新县辍学儿童的状况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。
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,胡子石村小学、陈店乡初中相继建成,让这块不毛之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于是,就有了追悼会那天,数以百计的河南人千里迢迢赶到北京,为他送行的原因。
“老将军”叶落归根,这是国人的淳朴心愿;而「五万余烈士待我归」,则是在红军时代以及抗战解放战争期间,受到的感召,成千上万的志士仁人,纷纷从军为国效力,但遗憾的是,却有超过五万人战死沙场。
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,的这几个子女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,所以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,的长子叫做李和平,是家中最大的一个,出生的比较早。
于是,抗美援朝之后,他便追随着他的父亲,去当了一名志愿军。他也像他的父亲一样,参与过上甘岭之战,为那一战抛头颅洒热血。
虽然在军队中的地位很高,但对自己的子女,却是从最基础的开始,进行最严厉的训练。
李和平就是靠着这样的形式,一步步走到今天,他已经退休,并且担任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的秘书长。
的二儿子李南征,李南征和他的父亲、母亲一样,都有着一颗爱国之心,选择了为国效力,不过和他的哥哥不同,李南征选择的是军校,而不是参军。
在军校里,他勤学苦练,苦练多年,终于在毕业后,一步步走到了北京化学副院长,并被提拔为少将,从这一点上来说,他的一生可谓是一帆风顺。
的长女李远征,从小就喜欢上了语文和文学。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,念了语文系,后来又被调往北京林业大学学习语言文学研究。
之后,她得到了去英国沃威克大学继续学习的机会,在最近一段时间里,她努力学习,并在沃威克大学取得了语言文学的硕士。
之后,他又在海淀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全面英语教学及语言研究工作,在英语及其他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,是一名杰出的学者。